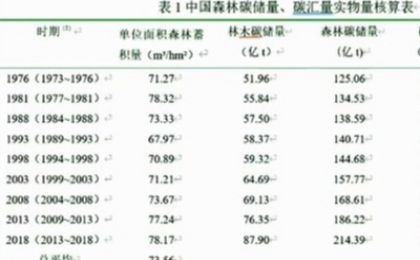——关注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现场
中国绿色时报4月3日报道(记者 迟诚 康勇军)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聆听历史的时钟,黑龙江森工林区“停伐”的嘀嗒声越来越清晰。
东北重点国有林区,在为新中国奉献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迎来了商业性采伐全面停止的历史节点!
3月1日早7时,零下18℃。黑龙江森工总局绥棱林业局八二林场的伐木工人马明林像往常一样,带上棉帽子,拿起油锯,从工棚出发,赶往采伐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积雪一尺来深,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太阳也照样明晃晃……这一天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区别,但马明林却突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距离4月1日全面停伐时日不多,黑龙江森工林区正在陆续收锯停伐,绥棱林业局只剩下八二林场的最后一个采伐班还有最后一天的采伐任务。当了22年伐木工人的马明林和他的工友们今天将最后一次挥舞油锯。
最近一段时间,“停伐”两个字成为东北国有林区的热词。街头巷尾,山上山下,人们都在议论着,盘算着。
对于160万龙江森工人而言,“停伐”就像一个早有耳闻但从未谋面的客人,明知他早晚要来,但是一旦得知他很快就要来了,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和惶恐,不知道这位客人的到来能够带来什么,改变什么?
2014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在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进行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国家林业局宣布从4月1日起黑龙江国有林区“全面停伐”。得知“停伐”的消息已经两个多月了,马明林心里经历了“心慌”到“接受”的变化。但日子一天天临近,“心里还是觉得越来越不得劲儿”,马明林脸上露出无奈的憨笑,常年在寒风中冻得通红的脸有些干。
“砍了50多年了,该歇歇了,该让林子好好养一养了”,他和工友们都明白停伐的道理。
中午11时30分,午饭时间到了。十几个伐木工人找块空地,围坐一起,找点树杈生了火,用树枝串上几个干粮在火上烤着。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这么多年,外人觉得艰苦,但马明林和工友们都已经习惯了。他们边吃边唠嗑,话题自然和“停伐”有关,无外乎“去哪”、“干啥”、“咋整”。
“老马,你说的养鸡那个事能不能行啊?”
“咋不行呢,你没看到有那么多人都养鸡、栽木耳、养蜂啥的,人家都比咱这挣得多啊!”
“那前期投入也得不少呢!”
“那倒是,但林业局不是说能帮忙提供鸡舍吗?”
“那还行。要是没有啥政策,不如出去打工。”
“打工你也就能干点体力活,啥技术也不会。”
“那也比在家呆着强啊!”
……
下午3时,马明林在事前勘察设计的预伐林木中,选中了一棵上面有红色标记的白桦树,他启动了油锯的发动机,大森林里的寂静瞬间不复存在。木屑飞溅,比以往更远,油锯轰鸣,比以往更响。这把油锯已经在这片林子里运转了十几年,它是马明林的“伙伴”。今天,马明林有些放任手中的油锯,他在和自己的“伙伴”告别,和这片森林告别,心情难以名状。
下午5时左右,工友们陆续从采伐点回到工棚。一个由塑料薄膜构建成的简易工棚里,已有师傅做好了晚饭,发面糖饼和豆腐汤,挺香。
住所很简陋,除了床和一个铁皮炉子,别无其他。所谓的床,其实就是一根根粗细差不多的木头排成一排,上面再铺上铺盖,高低不平,硌硌愣愣。围着炉子,打打扑克牌,唠唠嗑,再喝两盅,工友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简单且寂寞的漫漫长夜。
“估计没有人再来住了,这地方马上就要拆了。”48岁的唐继新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平时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一趟,嫌日子过得慢,现在要彻底回家了,还真是舍不得呢!”
“怎样看待停伐?”记者问。50多岁的老王问记者是否看过动画片《熊出没》,他说:“我那小孙女说我是动画片里的‘光头强’,‘光头强’不就是砍树的坏人吗?”
“国家需要砍树,我们就上山砍树;现在国家要保护树了,连小孩都知道砍树是坏事了,咱更得听国家的话了啊!”
下午5时50分,山上楞场,一辆装满了原木的大卡车正准备出发。上车前,司机陈师傅仔细擦了擦车前身挂着的“木材生产运输准运证”。夜行冰路,陈师傅开得很小心,他需要行驶近3个小时才能把原木运到贮木场。“停伐和改行都是早晚的事,晚停不如早停,晚改不如早改,人得往前看。”他心里很清楚,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在这条山路上拉木头了。
……
3月的东北林区里还满是冬天的气息。“停伐”关口,森工人和一个时代告别的心情难免有些复杂。留恋、迷茫、无奈、焦虑……当然,也有期待,期待着封锯后林区的春天能够早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