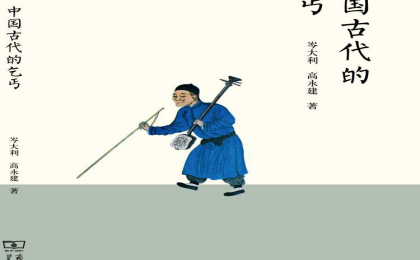生存第一,活着是创造的内生性动力
中国文化与创造力的现代解读之一
西方文化非常重视本体论,古希腊时代的代表性哲学家几乎各个都对本体论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基督教文明也重视本体,本体就是上帝,所以《圣经》的第一章就是《创世纪》。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中国文化不是没有本体论,但其位置在整个结构中并不重要。中国古代也有女娲造人的传说,但女娲的地位远远不能和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本体论,最重视的是什么呢?最重视的是修齐治平,它的基础在家庭。中国人对家庭有一种神圣感,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喜欢讲家国情怀。家和国显然不是一回事,这样的情怀处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差序伦理,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的基础在于农耕文化,小农经济。中国古代的创造力也特别表现在农耕基础上,不论任何一种发明创造几乎都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中。有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可以概括为治水文化。治水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另一面。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创造确实和治水有关,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和京杭大运河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四个最伟大的创造。虽然是治水,但它的内涵极其丰富。这里边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哲学、有科学、有技术、有习俗。可以说了解了这四大工程就了解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轨迹。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并非不发达,但它走的路数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中世纪教育是重视七艺的,后来变成了数理化,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古代科学主干是天、算、农、医。这四者并非全部与农耕生活有关,但显然其最重要的部分都深深植根于农耕文化之中。不仅如此,连中国古代神明都属于这个类型。古希腊古罗马也有很多神祇,但最重要的还是强力之神特别是战神和智慧之神。中国古代神话绝大多数远离暴力,而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包括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有巢氏——有巢就是盖房子;还有燧人氏——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甚至黄帝的几位妻子,她们的最重要贡献也在日常生活上。其中一位是中国蚕业的始祖,另有两位分别是镜子和梳子的发明人。
讲到创造力,既包括科技创造也包括社会创造,最重大的社会创造就是变革。中国的变革有两个重要的品征,一个品征是它一定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息息相关、血肉相关;一个品征是它必须有明确的受益人。中国三千年历史有过众多的社会变革,但最为成功的则是商鞅变法,最有成绩的则是张居正新政。以后的很多变革都没有取得商鞅变法那样的重大历史成就。商鞅变法的特点就是和人民生活,特别是和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史记》评价商鞅变法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很短的一段话包含了非常丰厚的内容。首先是生活安定,然后是经济富足,然后是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因为有了这些条件,所以乡邑大治。秦国产生了新的农民,也建立了新的制度,秦国吞并山东六国,其深厚的基础就在这里,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文化建构力与历史创造力。
根据我的研究,自春秋战国至今,中国有四项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这四项制度构成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框架。制度建构也是一种创造力,但它同样深深扎根于文化土壤当中。第一项制度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郡县制为骨架的中央集权制。这个制度统治和主导了中国文明两千多年。中国一切社会创造与辉煌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撑拒依存。第二项制度是以儒学经典为规范以考试机会均等为特征的科举制。科举制初兴于隋唐,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文化的一个空前大创造。18世纪中国科举制为西方所知,还让很多启蒙思想人物惊羡不已。第三项制度就是孙中山创立的共和制。第四项制度就是现在仍然在构建的现代市场体制。后两项制度已经进入现代化这一范畴,但前两项制度的建构显然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互进互动。
中国古代有过多次的改朝换代,但这些改朝换代并没有像欧洲那样造成罗马帝国的大分裂,造成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长达数百年的相互残杀与侵害。中国也有动乱,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统一和强盛才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主脉。中原地区曾数次被少数民族入侵,但结果毫无例外的成为了一种新的民族大融合。那么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是家庭;第二是土地;第三是科举。元朝统治者如此野蛮,但有了这三条,社会就安定下来;清朝入侵者同样野蛮,有了这三条就很快进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中国历史悠久,对这历史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评价不高。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但我要说即使真像他说的那样中国古代没有历史,但中国古代确有繁荣。这一点,黑格尔先生也是很难否认的。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属于超稳定体系,真正的革命难以发生,而这文化又有着巨大无比的自我修复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观点是,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特性,就是中国人非常热爱家庭,非常热爱生活。中国的辉煌常常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特别顽强和聪睿的精神,这个精神用两个字概况就是“活着”,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中国文化与创造力的现代解读之二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常重视和强调批判的作用。批判是没有界限的,可以理解为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批判的对象。西方人的这种文化和早已形成传统,并极大地影响了其历史发展轨迹。根据我的研究,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外部歧视。这种外部歧视在古希腊时代就有鲜明表示。雅典文明政治几乎人人都说是民主的典范、平等的典范,但它只限于对雅典内部自由人而言,绝对不包括非公民,特别是奴隶。奴隶没有人格,人格都没有怎么会有平等呢?雅典民主政体不能持久,古希腊文明无法得到直接延续也和这种外部歧视的文化品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也是这样,《旧约》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新约》的尺度放大了,但对于不同信仰者同样不能宽容。这样的情势一直延续到美国的建立。美国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最民主的国家,但美国的黑奴不能享受半点公民权力。西方人的这种批判精神常常是极端的,他们就是要打击旧的,创造新的;打击异类,宏大同类,对于异类一定要痛加消灭而后快,不但要在精神上给予清除,甚至在肉体上也要清除。
批判精神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自有其重要意义,并以此促成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丰厚土壤,技术革命在他们那里不是异态而是常态。美国一位重要的物理科学家泰勒,据杨振宁先生的回忆,他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拿出一个新的想法和同事分享,但这些想法常常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漏洞百出的,但他却浑不在意。这和我们中国人的学术价值表达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人做学问最害怕的是错,最忌讳的是硬伤,千万别错,错了太过丢人。但西方人不这样想,他的想法是我100个方案,正确了1个就够了,错99次没有关系。
中国文化的缺点在于内部歧视,这件事说来话长,因为不是本文的主题,暂且搁置。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理念不是批判而是中庸。单说中庸都不够,我们这里更重视的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独奏不多,合奏不少,上下调弦,举国互动。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对差的一概排斥 ,对坏的一定要消灭。我们也反对错的,但重点在于弘扬对的;我们也批判丑的,但重点在于弘扬美的。根据中国人的“道”的理念,世界并无创作者,无论神祇也好,人类也好,动物界也好,还是鬼怪也好,地狱也好,大家都生活在“道”的统领之中。包括皇帝在内,虽然皇权至高无上,好的皇帝称为“有道”,坏的皇帝就是“无道”。按照西方人的理念,能进入天堂的皆为好人,落入地狱的必有罪恶。但中国人完全不这样想。进入天堂的中国的那些神明也有很多缺点,就像调戏嫦娥的天蓬元帅那样,因为失其道也,终于变成了猪八戒;进入地狱的也有好人,不仅是鬼魂,包括狐妖蛇怪,都有最善良的灵魂存在。例如《聊斋志异》中那些美丽的狐仙,又如《白蛇传》中的那位白娘子。所以中国无论天上地下都是阴阳共存,优劣共在,既有恶神也有善鬼。我们智慧的中国祖先从来不认为所谓坏人可以、甚至应该被统统消灭掉的。我们的主张是要贤者在上、劣者在下,这个就够了。诸葛亮最著名的《前出师表》是怎么劝解后主的?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在这样的文化指导下,中国人的创造就形成了自己天人合一、上下互动的风格与特质。以文学艺术而论,汉赋非常发达,因为什么?因为从士人到统治者都喜欢这样的文体。汉武帝雄才大略,对汉赋痴迷。司马相如死了,汉武帝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派人去搜集他的遗稿。唐代诗歌繁荣,整个盛唐几乎成为了诗歌的海洋,何以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士人是平民,还是达官显贵还是贵为天子,都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唐代最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既爱书法又爱诗歌,以后的武则天、唐玄宗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诗歌创造只是诗人的事,格局未免太小了。只有拥有巨大的诗歌天地,才可能产生辉煌的诗歌业绩。
到了宋代,词又发达了,其原因和唐诗有许多相似之处。宋代著名词人中确实是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在。宋徽宗虽然是个坏皇帝却当真是个大艺术家,词也做得非常之好。其余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是词中高手,开一代风骚。宋代词人有高官也有才子,有改革者也有失意人,有僧侣也有道士,有疆场猛士也有风流骚客,有窈窕淑女也有关西大汉。如此七参八差,就像中国的中草药形成一个伟大的配方,在一个锅里慢煎细煮,药性才得以最充分的发挥。
有人概况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使用了“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这四个字未必可以概括,但不可否认的是“天人合一”所造成的创造力显然有其独到之处。
和而不同,包容是创造之母
中国文化与创造力的现代解读之三
西方文化具有纯、强、坚、大的风格。“纯”是纯粹,不容他人、他思、他教、他派介入;“强”是强悍,没有商量的余地,不兼容、不退让;“坚”是坚守,所谓底线思维,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古已有之;“大”是无限放大,西方的主义多,且一个主义出来便要竭力张扬,推向极致,天下万物唯我独尊,唯我独秀,唯我独正确。当然,这种状况在启蒙运动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中世纪时,排除异己一定是你死我活,启蒙运动后则主张:“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表达的权利。”虽然如此,在我正确、你不正确这一点上并没有回旋的余地。
以文学艺术为例,当古典主义盛行之时,天上地下都是古典主义。当浪漫主义兴起之后,古典主义成了过街之鼠,不但生存基础被掏空,连生存空间也不复存在了。
现代主义包括的门派极多,好像是大大不同于既往。其中包括存在主义、达达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荒诞派、印象派种种,但各自的壁垒分明,既是达达主义又是存在主义,或者一只脚站在意识流立场上,另一只脚站在荒诞派立场上,可以吗?笔者孤陋寡闻,未曾得见。
中国文化绝非如此。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争鸣固然争鸣,自由就在那里;到了盛唐时代,连争鸣也不需要了,盛唐显然是那个时空阶段最伟大的文明类型,既伟大又强盛,它不再需要争鸣,只是尽情表现。
即使在激烈争鸣时期,中国文化的表达与西方文化的表达也迥然有异,最激烈的争辩显然是孟子的辟杨朱,辟墨翟。杨朱主张“为我”,孟子不能接受;墨翟主张“兼爱”,孟子同样不能接受。孟子的观点是: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请不要以为孟子的表达方式很不雅驯,好像是恶语伤人。因为他的理念和杨墨迥然不同,那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也不要认为说杨朱是禽兽就是骂大街。因为孟子本人就说过:“人之异与禽兽者几稀!”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类和禽兽没多大区别。到了韩愈那里,情况又不同了,韩愈先生虽然以儒学自命,但他对墨子的看法绝对与孟子不同,他有一篇短文,写得非常经典。文章说:
儒讥墨,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尚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尚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
韩愈的结论是:“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盛唐时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一是王维,一是李白,一是杜甫。但细究其学缘,三者有显著区分。王维受禅宗影响很大很深,所以世人称之为诗佛;李白受道教影响最大,世人称之为诗仙;杜甫以儒学自命,被尊之为诗圣。这样的差异如果放在西方,那一定是水火不容的。但就这三位的关系而言,其实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尤其是李白和杜甫,还要相互欣赏、相互褒扬。李白并不认为杜甫迂腐,杜甫也不认为李白是旁门左道,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并世而存的诗坛巨匠。这样的风格无论在中国诗坛还是在中国文坛,都是顺理成章,不存在任何思想隔膜和风格障碍。当然,宋明理学对于佛教或道教有些不以为然,他们更推崇纯儒。尽管如此,但凡读过宋明理学著作的都知道那里面吸纳了很多佛教的内容,也借鉴了很多道家的思想。到了后世,至少在民间层面、宗教层面和社会层面,三者的严格界限完全被打破。比如北京西郊有一组古刹,称为西山八大处,其中一间庙堂之中就同时供奉着释迦摩尼、老子和孔子。三个人端坐一堂,好不惬意。
中国人的价值表达和风格理念,用一个词概括叫做“和而不同”。首先是“和”,和睦相处,价值宽容。其次是“不同”,中国人不怕不同,喜欢不同。阴阳就属于不同,有什么不好呢?不但没有不好,而且须臾不可废除。在中国文化看来,有阴阳而后有万物,这不仅是顺理成章的,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文学艺术的风格历来多种多样。比如宋词,有豪放派也有婉约派,豪放与婉约显然有着巨大的风格差异,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其实熟悉宋词的人都知道,豪放婉约只是概而论之,细细的去读,那风格还要更其千姿百态。李清照属于婉约派,她不大喜欢苏东坡,她有专文评价宋代词人词作,其中谈到苏东坡,说苏东坡的词不合音律,不过是句子长短不齐的诗歌罢了。但这批评并不激烈。严谨而不激烈,态度非常优雅,不但充分表现了这位女才子的精神风貌,尤其鲜明展示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与格局。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在古典小说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金瓶梅》与《红楼梦》,二者其实具有内在承继关系,但它们的风格差的太远了,所谓天高地远之别。《金瓶梅》是俗而雅,因其大俗而大雅。《红楼梦》则是雅而俗,虽然大雅,却可以通达万众。前者犹如佛头著粪,固然著粪,仍然是佛呀!后者可比喻为天女散花,虽然贵为天女,却关心民间疾苦,与生民同哀同乐。二者的风格差异可以说点点滴滴处处皆在。比如描写女性的美,《金瓶梅》是这样写潘金莲的:“从头看到脚,风流朝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朝上流”。俗是真俗,文学也是真文学。《红楼梦》全然不是如此,它形容凤姐的美貌,用语非常雅典,虽然雅典,却一点也不失生动。单说凤姐的眉眼:“两道柳叶吊梢眉,一双丹凤三角眼。”这个奇了。柳叶眉很好看,是中国古代对女性审美的公认的标准。然而,不是一般的柳叶眉,而是柳叶吊梢眉。丹凤眼更好了,龙凤之姿,何等高贵,然而却又是一双丹凤三角眼。这样的描写,不说别的,怕要难道天下多少丹青妙手。
创作如此,批评者同样如此。明清之际称小说批评为评点,而且评点俨然成了一种文体。评点《水浒传》的有金圣叹,评点《三国演义》的有毛宗岗父子,评点《金瓶梅》的有张竹坡,评点《红楼梦》的是脂砚斋。其中最系统、对当时影响最大、文笔也最美的,我以为是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其价值非常之高,甚至可以视之与《水浒传》本文为艺术之双璧。这里引一段他评说《水浒传》人物风格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人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约,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这里说的是写人,其实不仅仅是写人,我在不少地方曾经推荐过唐人司空图的“诗品”,用它来证明中国文学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有一个时期,只许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那样的追求未免太过单调了。司空图的“诗品”主要是讲风格,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和而不同”这个角度去理解他的“诗品说”,他不是讲1种风格,也不是讲5种风格,而是一口气讲了24种风格,整整的写了一本书。从风格学的角度看,特别是从“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去理解,这书实在是非常精彩。
“和而不同”体现了一种博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中国的伟大文学作品常常与兼容性密不可分。最著名的代表应该是《红楼梦》。《红楼梦》是空前的历史文学巨著。它非常伟大,同样非常兼容,因其兼容而伟大,又因其伟大而兼容。这样的中国文化传统显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道重于技,自由是创造的最高境界
——中国文化与创造力的现代解读之四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其共同之处在于创新求变,精益求精,然而,变与变也有别。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不薄今人爱古人”。西方人强调的是批判旧物以图新知。
在精益求精这一维度上,双方也各具风采,自成一脉。西方文化特别重视数学和逻辑的价值与作用。西方现代管理学非常强调量化管理,这一传统其实渊源久矣。重视数学必然重视事物的量化分析,重视逻辑又必然重视理性。对于数学的重要性早在柏拉图时代,就有诸多经典论述,而逻辑学在西方的历史同样久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你再抒情,再有感染力,不合逻辑,对不起,不能认同。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但于逻辑这件事不甚讲究,古代也有重要的逻辑思想和发现,但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性的学问。中国古代数学也非常有特色,有成绩,但地位远不如西方那般重要。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技进于道,情景交融。一方面讲技,一方面更要讲道。有技无道,只是匠人;有技有道,才是大师。虽然也重视理性,但不可以唯理独存,强调的是有情有理,不但合情而且合理。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贵在情理之中,美在情理之中,妙在情理之中。
以烹调为例,西方烹调也非常有成就,他们是有精确的量化标准的。盐要几克,油要几克,一一标明,不允许差错。中国烹调技艺世界闻名,然而自古以来没有那样量化的传统。大师说了关键在于火候,但你如果问火候是温度多少?就是你蠢了。盐也是这样,著名的菜谱中,讲到盐,常常表明加盐少许,少许是多少?你非用天平来称,也是你蠢。这样的追求并不适用于一切现代领域。因为它的经验性很强,数字概念模糊,但结果往往很奇妙,口味往往很独特。虽然它不见得适用于一切现代领域,却又非常适用于艺术领域,情感领域,心理领域,也与某些重大的现代科学成果天机巧合,别有通路。例如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光学中的魄力二相性,联想到量子力学,联想到测不准原理。形象的表达,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只薛定谔的猫咪。
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强调化境。化境乃是最高境界,所谓境由心生,巧夺天工。技术也是必须的,练习书法还必须临帖,学习戏剧更要一招一式。昔日北京著名小吃店烤肉宛的老板请齐白石先生题写店名,白石先生在落款上特别写明“古无烤字,老夫自我作古”。可见传统规范的重要性。又如这些年因为青春版《牡丹亭》走红的昆曲,对于唱腔道白的发声都非常讲究,可以说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必须有师承。然而,这些表示的是艺术的学习与过程,到了臻于化境的时候就不再是如此一板一眼的模仿,而是达到一种随心所欲的发挥,从而进入了自由境界。例如王羲之的字,梅兰芳的戏,瞎子阿炳的演奏和周作人的文章。
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他的字当然非常有规范。一方面是自由挥洒,一方面又法度森严。固然法度森严,法度不是成为障碍而是成为艺术的支点。王羲之一声写过非常多的“之”字。这些“之”字或长或短,或瘦或肥,或疾或徐,或大或小,然而绝对没有重样的。有专门研究者把这些“之”字集在一起,让人看了倍觉千姿百态,凤翥龙翔。
梅兰芳自然是戏剧大师,他对戏剧的影响可以说无与伦比。他访问苏联的时候,有著名导演观摩他的演出,发现他同一出戏每次的表演都有变化,觉得很奇怪,就向梅先生请教。其实,这既是中国京剧以及诸多中国艺术的一个特色,又是梅兰芳大师达到极高的表演境界的自由表达。京剧表演以及很多的剧场表演形式非常强调和观众的互动,因为要和观众互动,所以那表演节奏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时就要快些,有时就要慢些。在中国这些艺术大师中,梅先生还是风格最为优雅平和的,周信芳先生不但每次演出的动作可能不同,有时连唱词都改了,道白都改了。观众不但不反感而且觉得愈发新奇,还要更起劲地喝起彩来。现代的很多京剧演员只会按照特定的程式做戏,技艺不能说不纯熟,但纯熟的只是技艺而已,情少了,人物的特色少了,自由境界更谈不到了。
前些时候,我听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讲座,讲到“二泉映月”,那作品只有一段极其珍贵的录音,后来的人将这录音奉为不可或改的经典。宋瑾教授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当初录音的时候,阿炳曾经问录音者,你们想录多长时间?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二泉映月”是可长可短的。到了阿炳那样的演奏境界,“二泉映月”只是一个框架,演奏人则是这框架中的精灵。他可以在这框架中做出各种各样非常优美的舞姿,而这舞姿则因观者的变化而变化,因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二泉映月”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美景,而是意境丰富、万千变幻。这一点和西方交响乐截然不同,但也因为这不同,才更鲜明地表现出中国民乐的特点和优长。
还有周作人先生的文章,文章的长短依常理论,是应该有一定之规的。俗话所谓“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适合写短篇小说的不能硬拉成中篇,那就水了;适合作长篇的,也不能硬挤压成短篇,那就干了。但周作人先生文章的妙处,在于他可以随着编辑的要求从容起舞,自由表达。据说向周先生约稿,他常要问的是需要写多少字,要3000字就写3000,要500字就写500。中国的某些散文名家,看其单篇也有特色,放在一起,常常是一个路数,连着看下去感觉就负面了。周作人的文章不会这样,他的散文集有好几大本,从来不会给人以厌烦感。因为他的那些作法,虽然风格平淡如水,却能做到千变万化,妙在其中。
如前所述,创造的生命原本鲜活,唯有鲜活的生命才会永远追求,永不满足。文化似乎是恒定的,但日日时时也在变化。中国文化与创造力可以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变数,这个历史的变数恰逢当今时代,必定要经过类似凤凰涅槃这样的浴火重生。对于中国文化与创造力而言,有三个重要因素是绝对不可以轻视,也绝对不可以绕过的。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岂止如虎添翼而已。
第一个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市场的力量无比巨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绝对贫困的小农经济国家,唯有市场经济可以变贫困为富足。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中国文化的创造力一定会达到新的量级和新的层次。
第二个要素是法治。有人说中国古代属于人治,其实不确,中国古代属于礼治。那时代也是辉煌的,但礼治时代过去了,法治时代必定到来,而且唯有法治才能最有效的保护创造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创造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对知识产权的真正有效的法律与法制护持。
第三个要素就是现代化。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政治要现代化,创造也要现代化,连文化都要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在现代化的这个大题目下,才能做好中国当代这篇大文章。进而使中国的创造与创造力更具文化性,也使中国文化更具创造性。